提到書寫劍橋的當代文字,多數人會想起徐志摩《再別康橋》、《我所知道的康橋》和陳之藩《劍橋倒影》。後者更因為當年書寫頗獲大眾青睞,因此去年天下遠見將他一小部分新的文章和一堆舊文,出了本《散步》。陳之藩與徐志摩主要不同的地方,在於他是科學出身。可這點不代表所有念自然科學的人都會喜歡陳之藩的散文。就有一位物理界學者跟我說,陳之藩的文字很好,但他寫的東西未必讓人同意。他去過劍橋,但沒有陳之藩那種感想。
看過別人的文字,而被誤導對一地印象的,是常有的事。林太乙在〈都怪徐志摩不好〉就提到,她被徐志摩歌頌西湖的文字所吸引,因此過度期待,導致她看了實際情形後,大失所望。類似的經驗我也有,於是後來就不太看別人寫的遊記,等回來再說。
因為現下出國方便,電腦幫助書寫容易,遊記書因此越來越氾濫。對書寫出國見聞最謹慎的,可能是李銳了:「美國那麼大,到一個地方寫一本書,是什麼意思?」但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珍惜文字和謹慎下筆的觀念,於是鍾文音稱為「畢業紀念冊」的旅遊書大大氾濫。去年更因為《我的心遺留在愛琴海》的暢銷,更促成許多作者和出版社不自量力,以為好賣而跟著推出圖文並陳(數位相機太普遍了)的旅遊書,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。但擁有這種到一個地方寫一本書來紀念的人,仍不在少數,網路上就可看到隨便起鬨的人,覺得圖片還不難看,便出餿主意要對方出書,不知《我的心遺留在愛琴海》只是特例而已。的確會有分不出內容好壞的消費者去買,只是銷售數字和作者、出版社理想相去甚遠罷了。台灣一年有四萬多本新書,每本書能分到的能見度有限,這些前仆後繼的烈士,徒然進行一種十分不環保的舉動。在網路上留個記錄也就罷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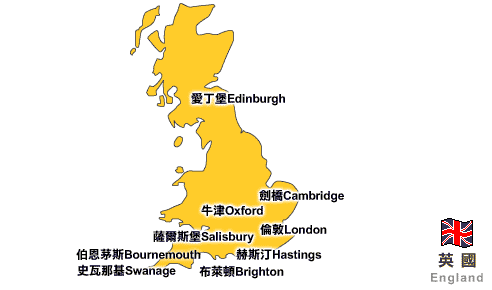
拿著《劍橋流水—科學‧人文‧大不列顛》,我第一件事是翻閱圖片,想知道自己是否全然遺失對劍橋的記憶。由於還能辨識作者劉兵並未清楚註明的照片地點,而且有些地方的氣味還保留在我腦海,看來英國的印象仍在。
劉兵的這本遊記,主要是從他的科學史背景來寫。因此他逛了不少和科學有關的博物館等,和我在英國主要看藝術博物館,大大不同。他也提到一些我去過的藝術博物館,就如他自己所說「走馬看花」,他提到藝術的文字,也沒花太多力氣。倒是科普的部分,還算有意思。英式教育的部分,也讓我懷想良多,早幾年曾想過去英國念Ph. D,更是不由自主地被那種開放式的學習所吸引。基本上,劍橋大學作為一個大學城,就是處處都可學習的地方,不管是博物館、戲劇、酒館等。儘管我在那的日子很短,但那些部分都曾豐富我的心靈。尤其是其它台灣同學都跑去當血拼大王時,我一個人去費茲威廉博物館(The Fitzwilliam Museum),看到令我驚奇的展品時,那種心情真是難以形容。走筆至此,不免再度感嘆勞基法對勞工保障之少,還要八年、十年以上,我才會有長到可以再去歐洲看看的特休假。
我特別有興趣的,該是他提到Grantchester的下午茶。那年我在Grantchester的果園(The Orchard)嘗到高熱量的scone,雖不驚為天人,但讓我偶爾有親近這類極易導致肥胖的點心的衝動。喜歡肉桂味,更是在英國培養出來的。此處的下午茶位於果園,椅子上自然有許多鳥類排泄物,跟康河岸旁的「特產」有異曲同工之處。許多人只見康河河岸綠草如茵,鴨子、鳥類遊過、飛過,甚是愜意,殊不知,那草地處處都是「黃金」。當年我坐在草地上,發現附近有什麼時,驚慌失措到差點滾進康河裡。
連著兩篇〈墓地裡的名人〉,讓我覺得這個作者還真是有點怪,但怪的滿有趣。劍橋的確處處有名人的痕跡,墓園也不例外。當年我要照Grantchester附近的墳墓時,旁有台灣人一副拍了就會有鬼魅上身的樣子,逃之夭夭。但劉兵不但拍了十幅以上,還拍了貓站在墳墓上的樣子,煞有意思。看這些英國墳墓的圖片,不免有些感嘆。中國人的墳墓文化,很難讓人在幾百年後,站在墳墓旁邊說:「這是幾世紀的□□家某某某安息之處」。華人總有種畫地為王、圈地亂葬的習俗,尤其是所謂「風水好」的地方,更是變成「亂葬崗」的景象。好比我家對面的山頭就有個墳墓,每逢清明,他們子孫祭拜打掃過後,就會開門可見,直到過一陣子,樹葉和草長出來,才可以遮住。以前騎車上下班,總要經過墳墓山,滿山的墳墓,方向不一、大小不一,毫無美感可言。好在台北市政府警覺土地資源不足,最近開始提倡樹葬等環保葬法。但我始終認為,墳墓是台灣最難改變的建築文化之一。而且民間信仰總有「燒」的習俗,不只燒給自己先人,還要燒給土地公求富貴,每年燒掉的紙量可觀,引起的大小火災也動用消防資源,最要緊的,或許是最後反倒失去那種追思的心情。江湖術士不時傳授的往生慣例,更是強烈的一套「怕後人忘記」的哲學,好比子孫不拜就不孝,不孝就不會富貴。但達爾文父子的墳墓都沒像華人這樣講求「背山面海」等陰宅風水,後代照樣有自己的成就,而且現代多半講求各人的能力,父祖的庇蔭早就不像幾世紀前那樣有力了。究竟要到何時,我們才有像英美電影裡那種整潔美觀、不求頭角崢嶸的墓園景象,讓人能夠真正發自內心的追思,而不是靠外物來制約人的行為呢?
《劍橋流水:科學‧人文‧大不列顛》
作者:劉兵/著
出版社:未來書城 (溫世仁的出版社)
初版日期:2004 年 01 月 01 日
看過別人的文字,而被誤導對一地印象的,是常有的事。林太乙在〈都怪徐志摩不好〉就提到,她被徐志摩歌頌西湖的文字所吸引,因此過度期待,導致她看了實際情形後,大失所望。類似的經驗我也有,於是後來就不太看別人寫的遊記,等回來再說。
因為現下出國方便,電腦幫助書寫容易,遊記書因此越來越氾濫。對書寫出國見聞最謹慎的,可能是李銳了:「美國那麼大,到一個地方寫一本書,是什麼意思?」但絕大多數人都沒有這種珍惜文字和謹慎下筆的觀念,於是鍾文音稱為「畢業紀念冊」的旅遊書大大氾濫。去年更因為《我的心遺留在愛琴海》的暢銷,更促成許多作者和出版社不自量力,以為好賣而跟著推出圖文並陳(數位相機太普遍了)的旅遊書,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。但擁有這種到一個地方寫一本書來紀念的人,仍不在少數,網路上就可看到隨便起鬨的人,覺得圖片還不難看,便出餿主意要對方出書,不知《我的心遺留在愛琴海》只是特例而已。的確會有分不出內容好壞的消費者去買,只是銷售數字和作者、出版社理想相去甚遠罷了。台灣一年有四萬多本新書,每本書能分到的能見度有限,這些前仆後繼的烈士,徒然進行一種十分不環保的舉動。在網路上留個記錄也就罷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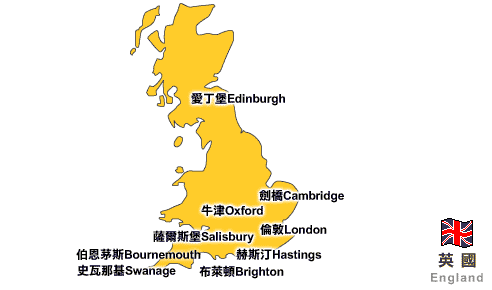
拿著《劍橋流水—科學‧人文‧大不列顛》,我第一件事是翻閱圖片,想知道自己是否全然遺失對劍橋的記憶。由於還能辨識作者劉兵並未清楚註明的照片地點,而且有些地方的氣味還保留在我腦海,看來英國的印象仍在。
劉兵的這本遊記,主要是從他的科學史背景來寫。因此他逛了不少和科學有關的博物館等,和我在英國主要看藝術博物館,大大不同。他也提到一些我去過的藝術博物館,就如他自己所說「走馬看花」,他提到藝術的文字,也沒花太多力氣。倒是科普的部分,還算有意思。英式教育的部分,也讓我懷想良多,早幾年曾想過去英國念Ph. D,更是不由自主地被那種開放式的學習所吸引。基本上,劍橋大學作為一個大學城,就是處處都可學習的地方,不管是博物館、戲劇、酒館等。儘管我在那的日子很短,但那些部分都曾豐富我的心靈。尤其是其它台灣同學都跑去當血拼大王時,我一個人去費茲威廉博物館(The Fitzwilliam Museum),看到令我驚奇的展品時,那種心情真是難以形容。走筆至此,不免再度感嘆勞基法對勞工保障之少,還要八年、十年以上,我才會有長到可以再去歐洲看看的特休假。
我特別有興趣的,該是他提到Grantchester的下午茶。那年我在Grantchester的果園(The Orchard)嘗到高熱量的scone,雖不驚為天人,但讓我偶爾有親近這類極易導致肥胖的點心的衝動。喜歡肉桂味,更是在英國培養出來的。此處的下午茶位於果園,椅子上自然有許多鳥類排泄物,跟康河岸旁的「特產」有異曲同工之處。許多人只見康河河岸綠草如茵,鴨子、鳥類遊過、飛過,甚是愜意,殊不知,那草地處處都是「黃金」。當年我坐在草地上,發現附近有什麼時,驚慌失措到差點滾進康河裡。
連著兩篇〈墓地裡的名人〉,讓我覺得這個作者還真是有點怪,但怪的滿有趣。劍橋的確處處有名人的痕跡,墓園也不例外。當年我要照Grantchester附近的墳墓時,旁有台灣人一副拍了就會有鬼魅上身的樣子,逃之夭夭。但劉兵不但拍了十幅以上,還拍了貓站在墳墓上的樣子,煞有意思。看這些英國墳墓的圖片,不免有些感嘆。中國人的墳墓文化,很難讓人在幾百年後,站在墳墓旁邊說:「這是幾世紀的□□家某某某安息之處」。華人總有種畫地為王、圈地亂葬的習俗,尤其是所謂「風水好」的地方,更是變成「亂葬崗」的景象。好比我家對面的山頭就有個墳墓,每逢清明,他們子孫祭拜打掃過後,就會開門可見,直到過一陣子,樹葉和草長出來,才可以遮住。以前騎車上下班,總要經過墳墓山,滿山的墳墓,方向不一、大小不一,毫無美感可言。好在台北市政府警覺土地資源不足,最近開始提倡樹葬等環保葬法。但我始終認為,墳墓是台灣最難改變的建築文化之一。而且民間信仰總有「燒」的習俗,不只燒給自己先人,還要燒給土地公求富貴,每年燒掉的紙量可觀,引起的大小火災也動用消防資源,最要緊的,或許是最後反倒失去那種追思的心情。江湖術士不時傳授的往生慣例,更是強烈的一套「怕後人忘記」的哲學,好比子孫不拜就不孝,不孝就不會富貴。但達爾文父子的墳墓都沒像華人這樣講求「背山面海」等陰宅風水,後代照樣有自己的成就,而且現代多半講求各人的能力,父祖的庇蔭早就不像幾世紀前那樣有力了。究竟要到何時,我們才有像英美電影裡那種整潔美觀、不求頭角崢嶸的墓園景象,讓人能夠真正發自內心的追思,而不是靠外物來制約人的行為呢?
《劍橋流水:科學‧人文‧大不列顛》
作者:劉兵/著
出版社:未來書城 (溫世仁的出版社)
初版日期:2004 年 01 月 01 日
留言